本文并非一篇学术研究或新闻报道——围绕病毒源头的挖掘困难重重,需要严谨的科学求证。我不过结合了自己的经历,撷取了在我们全力追求答案的过程中,能够延伸思考的那部分作出分享。希望在科学真相到来前,我们的思考不要停止,可以往前多走几步。
2月2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华南农大等机构发表预印文章称,通过对93个新冠病毒样本的分析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可能是从其它地方传入,拥挤的市场只是促进其传播。
论文中这组图表说明了几种进化和传播路径的可能性。广东和美国都存有嫌疑,不过还是武汉的可能性最大。2月8日,一篇管轶为联合作者的论文,对中间宿主做出猜测:“新冠肺炎暴发暂时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野生动物销售可能是人畜共患病的传染源。蝙蝠可能是源宿主。论文报告了在中国南方的反走私行动中查获的马来穿山甲(Manisjavanica)中发现与新冠病毒相似度极高的冠状病毒。穿山甲应被视为可能的中间宿主。”论文摘要
两篇论文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的看法貌似相左,但其实都认为这个狭小而环境复杂的地点对与大范围传播有直接关系。同时管轶的论文发现,尽管马来穿山甲病毒和致疫病毒关系紧密,而其他的亚洲野生物种同时存有中间宿主的嫌疑。不管是谁,都还是无法解释完整的演变路径和源头。不过管轶的研究让我想起去年我们做的一个报道,关于广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首批无害化处理的马来穿山甲。还记得当时适度删减了血腥镜头,即使如此,还是出现了大量穿山甲尸体。记者梁凡和我确认:这五吨动物尸体,实为近几年来积累多次缴获的走私野生动物,主要为马来穿山甲,另有猴子和蟒蛇;所以,这其中应包括了报告中提到的年8月到年7月缴获的走私马来穿山甲,之后部分冻体作为科学研究样本保存了下来。眼前的这批正被“无害化处理”的穿山甲,很可能体内存有冠状病毒。视频来源:界面新闻·观见,崔梁凡摄。中缅和中越边界都是走私犯携带濒危动物流入中国的主要门户,穿山甲、黑熊、老虎、大象等数不胜数。多年前昂山素季当选时,我曾带一行八人去做了边境系列报道,见识了小勐拉等地区的走私产业。除了勐拉,密支那、迈扎央等地都是重要枢纽,纪录片导演赵明也曾跟我展示过迈扎央阳光下的黑市以及遍地的野味餐厅。
绿发会曾宣称,中华穿山甲“功能性灭绝”,自然专家霄迪也与我谈到了中国已很少见本土穿山甲。陈婉莹老师和Karen等数十位记者合作的年度穿山甲报道里提到:“大量需求成为了杀手,把全球的穿山甲推上灭绝之路。”图片来源《“穿山甲报告:走私至灭绝”(TraffickedtoExtinction)》全球深度报道网人们为何对穿山甲趋之若鹜?首先,穿山甲是中药。中药在这一次抗击疫情中表现抢眼,屡现新闻头条;而见不得光的穿山甲,医书上说可治中风瘫痪,麻木拘挛,有助于缓解脑梗等疾病。医院ICU主任谈曾接收“零号病人”的报道已经撤稿,文章提到,这是一位有脑梗的老人,且从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一时间猜测四起。我并非在指责购买者。若很近的亲友不幸染上顽疾,对于各类治疗办法,尤其是低风险的,为什么不试一试?正因为此,很多始于名贵药材的偏方常年拥有大量市场。图片来源《“穿山甲报告:走私至灭绝”(TraffickedtoExtinction)》全球深度报道网
比起入药,吃野味儿就是另一回事了。蔡澜曾说,“吃野生动物没有意义。野味之所以是野味,正是因为没个性,不够好吃,否则早就被驯养成家畜。”陈晓卿补充,“(对于食材)厨师也得不到每天的训练”。人们在尝试皮糙肉厚的野味之时,除了心心念着中医药膳文化中的“以形补形”和“越野越补”,还有瞬间膨胀起来人类天生对于稀缺事物的好奇心,为满足这份好奇心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最后还要转变成微博上的炫耀帖,或商贾和大员之间交往所依托的炫耀型消费。我在特罗姆瑟国际电影节(Troms?InternationalFilmFestival)看了中国电影《完美现在时》(Present.Perfect.),一部仅用直播平台内容剪辑而成的“桌面纪录片”,片中有吃虫子的中国人,也有这段台词。
但这些都不是我吃蝙蝠的原因。是的,我吃过蝙蝠。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经常下到偏僻的地区,拥有无数“机会”进食野生动物,甚至像躲不掉的主人敬酒一样,通常客人不能拒绝。还有更特殊的情况,就是糊里糊涂地吃下不明食物。我的蝙蝠,就是这么入肚的。村民盛情招待我的晚餐(如非标注,图片均来自作者)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深处住的那几天,热情的村民每顿饭都要用河水给我煮一碗胶状且发酸的木薯粉,相比之下,一条通体乌黑的“鲜肉”颇具诱惑,一口下去,筋斗,有肉香味儿。第二天,村子里的大姐,特意把它拿出来,告诉我昨晚吃的是什么。
当我得知前一晚误食的黑肉是蝙蝠(果蝠)时,那一股恐惧似乎伴着病毒一起蔓延到了每寸肌肤。我以飞一般的速度打开手机紧急求助远方的医生和健康领域专业人士,在得悉野味儿经高温烹煮后直接感染的可能性极低后,方才松了口气。被迫回想起这些经历时,我下一个念头就是:“那次回国后有没去过武汉?”最新的几篇论文尽管结论不甚相同,但蝙蝠作为源头宿主的头号嫌犯,倒是没有争议。被认为是SARS、埃博拉、马尔堡等头号传染病源头的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人类已知就有近两百种。是什么造就了这个飞行的病毒皿?古老的蝙蝠作为会飞的哺乳动物,拥有超高的新陈代谢率,持续肌肉运动让体温持续在40摄氏度以上,在经过千百万年高烧不退的进化后,高温即可杀死病毒,也让蝙蝠拥有了DNA损伤修复超能力,这也导致了蝙蝠们平均五十岁的超常寿命。病毒们再也杀不死蝙蝠,于是选择安静地留在了蝙蝠体内。我曾去过很多洞穴,看过穹顶之挂满蝙蝠,那种恐惧难以言表。在冬眠中,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实际上许多病毒可以被热血动物们较快清除,但倒挂的冰箱们就不一样了。一旦醒来,它们就是飞行的天然病毒库。那为什么当地人天天吃“危险物种”却没事呢?我私下咨询过《知识分子》的主编叶水送,得到的答复是,“有些病毒只在特定的蝙蝠身上传播,而当地人即使感染过(弱毒性的)病毒,也只是局部性的,不会传播到其他地区。”人类不可能阻止地球上继续孕育出病毒,但是,正是半自然的天然隔离机制,给了物种间留出了缓冲地带。一想也是。千万年来,土著人和大自然相安无事,就算是中国人对野生动物又是吃、又是入药的,也早有历史;而打猎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石。大规模传染病如若总是频发,人类可能早该灭绝了,或者进化成了不会飞的病毒库。巴布亚新几内亚特鲁布地区卡马索村村民的日常食物
“恒河水治百病”这句话正是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写照:自身抗体的形成,是生物们都有的本领。住在蝙蝠洞或蝙蝠栖息地附近的村民身体里发现过大量病毒抗体,而这种单一环境发展出来的野生病毒的毒力并不强,暂时不会让人得严重的疾病,给了人类应对的时间。其实不止是边界居民或猎人,当年SARS以后,很多野味市场的从业人员身上都查出了SARS抗体,说明他们也被感染过,但他们并不生病。生病死亡的反而是一般人群。就如当年挤奶女工都得过牛痘,一辈子不得天花。甚至除了“人兽共患病”(Zoonoses),还有“反向人兽共患病”(Zooanthroponosis)。李迪强教授在神农架接受纪录片《熊猫回家》采访时说,他曾发现其他地区有人传染给猴群疾病并大范围传播,以致引发种群灾难的例子。不过这些人有抗体,不代表更多的人不会感染。叶主编还说:“武汉、香港、广州之所以大范围传播,一个这里有很多迁徙候鸟,二是这些地方人群流动大,容易交叉感染,造成的公共健康危害也很大。”正是人类不断发展壮大的养殖、运输、储存动物的能力以及更大的居住密度给病毒创造了各种融合机会,很多时候还可以是跨物种的合成。在高度社会化的人居场所,环境空前复杂,尤其在野味市场这种肮脏的狭小空间中,俨然一个杂交病毒池。即使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源发地,也一定是个领域疫病高速扩散的中心。人类文明发展中那些被依次驯化过的野味,也就是如今温顺的家禽、家畜,与野生同胞们在这里不期而遇。然后,惊变。除了海鲜市场,过度放牧或圈养同样让家禽、家畜进入蝙蝠栖息地。例如在马来半岛导致百人死亡的尼帕病毒,来自侵占了果蝠的家园后被果蝠感染的家猪;同样,MERS起源于饲养的骆驼;亨德拉病毒由家马传播;天花、麻疹、肺结核都来源于人类养殖的牛。在《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书中,内森·沃尔夫认为:微生物净化使人类更脆弱,这也是印度人抵抗力强的原因;从抓捕动物到驯养家畜,人类由游牧转型为定居,隔断了与野生世界的连接;而人类与家畜的亲密接触、大规模固定社区的发展,又让人类置身于一个将更易爆发流行病的世界。无论交通物流还是畜牧业,人类没有可能让现代化逆转。但寻找阶级敌人的任务是不停止的。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大量野生动物如绝大多数的蝙蝠、鼠类、鸦类等传播疫病高风险物种并不在保护管理范围中。即对其猎捕、人工饲养、利用的行为,不能依《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管控。2月4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提出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九个建议,其中第二条建议提到:“将地方保护的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传统的“三有”动物,以及那些可以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则可以考虑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允许科研利用和生态灭杀。”不同于对尸体的无害化处理,这一次用“生态灭杀”来一次性解决问题的建议,引起了学界和舆论(尤其是穿山甲和刺猬这些可爱物种的拥护者)不小的质疑:其实,大家自小就应学过生态链和生态平衡一说:都这么久了,地球上没有谁是多余的,缺失一环就会造成失衡,可能引发生态灾难;即使是蝙蝠,作为夜行性昆虫(比如可以传染疟疾的蚊虫)的主要捕食者,还有一些承担植物授粉和种子传播的责任。退一步来说,历史上的主动生态灭杀似乎都不太成功,例如澳洲野兔,而利益或食欲驱动的杀戮,似乎才是动物灭绝的有力手段。历史上人类曾经尝试过大规模捕杀蝙蝠的试验,基本以失败告终,比如为了防止狂犬病,人们在南美洲用上了毒药和炸药,不但无法彻底清除蝙蝠种群,不断地侵扰反而加剧了带毒个体更大范围的迁移流动,为人居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安全风险和难以预计的生态系统退化。在单一个体身上的侵扰有时甚至可以激发卫生风险。如同马来穿山甲身上的蜱虫,正是受外来刺激后才爆发;再比如传染性腹膜炎病毒也是一种猫身上常见的冠状病毒,在受到侵犯和外界强烈刺激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猫的免疫系统失效,从而使其患上高致死率和高传染性的猫传染性腹膜炎。似乎一切都在指向,“生态灭杀”既不人道,也不科学。然而,我们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年的那个夏天,随着隔离救治,非典疫情终结。但在同年的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管轶坚持认为,就如同香港杀鸡以平息禽流感,只有彻底“灭杀”市场上的中间宿主——果子狸,才是唯一根治的办法。在钟南山院士的帮助下,全国进行了果子狸大清洗。自此,非典在广东绝迹。回到最开始的论文,为什么管轶来提醒“中间宿主”是谁很重要?无论穿山甲有多可爱,人们也知道生态灭杀其他物种并非是自然之道,但如果穿山甲真的就是那个“中间宿主”,曾成功在广东根除SARS的功臣管轶大概率可能会讲,灭杀穿山甲能够根除眼下的危机。这个时候,我们应如何选择?或许对大自然来说,人类才是越界的那一位。从“除四害”,从有了“益虫”和“害虫”之分起,我们就早已有了明确的生存是非观:其他物种的利益低于自身的利益,眼下的利益紧迫于未来付出的更高代价。山地大猩猩邱嘉秋摄
我在卢旺达和刚果(金)的边界丛林中,近距离接触了山地大猩猩。研究表明,这些类人灵长类动物身上,携带的不是HIV病毒,是艾滋病的变异源头SIV病毒(猴免疫缺陷病毒)。人类的不明接触最终导致了HIV在人类社会的传播。当地的传言这样讲:刚果河的上游孕育了埃博拉,下游诞生了艾滋病。这条地球上水最深的河流,留下了那些最深的疑问。鸟瞰刚果河
英国地质学家科林·沃特斯曾说,“塑造地球的主要地质力量——它不再是河流、冰或风了,而是人类”。刚果河流经的刚果盆地雨林曾被喻为“非洲之肺”,不可持续的非法砍伐和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加速全世界仅存的地球之肺们不可逆转的发炎与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指示病例是住在几内亚美良杜村的一名两岁男童EmileOuamouno。林业专家霄迪引用的数据表示,偏远的美良杜村周边森林区域大多已因外国采矿业和林业作业遭到破坏,森林损失约超过80%,并使可能受到感染的野生动物以及被认作病毒天然宿主的蝠类动物更加靠近人类的居住区域。在男童出现症状前,有人曾看到他在后院玩耍,临近的一棵空心树内栖息有大量蝙蝠。热带雨林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池,包含了地球上的大多数动植物,几乎所有活物都携带病毒,因此雨林也是最大的活性病毒储备池。而森林的缓冲地带,被人类不断毁坏、侵占或侵扰。原来的野生动物,例如蝙蝠,不得不离开千万年来的栖息地,在雨林的边缘区域,被动地与新世界近距离接触。自然,病毒也跟着一起亲近人间。对病毒而言,新世界如此广阔,没有理由不在毒性最强的时候尽力传播。于是前文我们提到的种种可能的惊变故事,开始竞相上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被非法砍伐,改种棕榈等经济作物。《被砍断的地球肺——跨国木材贸易调查》邱嘉秋摄
古老的边界一直是由人类和动物共同把守的,易感的或有抗体的,既是各自种族的面壁者,也是不同物种间的谈判官。吃野味的一线还是在原始森林的边界,世代居住的人们用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来满足生存需要。边界的生物构成屏障群,真正出错的地方在哪里?既不是蝙蝠也不是穿山甲,而是业已破损的森林边缘。是时候划分边界了。跟灭杀“中间宿主”等野生动物的伦理困境不同,人类停止非法和过度砍伐森林,牺牲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人一小段时期的利益,换来的则是人类和其他物种彼此之间更大的生存机会。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不得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而涉及到林业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重要议题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5)原定计划年在中国举办,审议“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新目标,这将是《公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之一。回到吃野味儿,不难发现,“禁食”只是一个基础性倡议。2月9日,自然之友等八家环保组织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建议,秘书长张伯驹对我讲:“立法目标回归为确保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从而保障生态安全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禁食野生动物。成立野生动物保护局。”2月24日,据新华社消息,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疫情之后,我猜很多人看到野味儿都可能唯恐避之不及。不过也难说,人们忘性大。//作者:邱嘉秋//编辑:Alexwood在这次疫情中,你是否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你和周围的人产生了怎样新的关系,你获得了哪些观察和思考?如果你有想法想要分享,请发送电子邮件到tougaoyishiyis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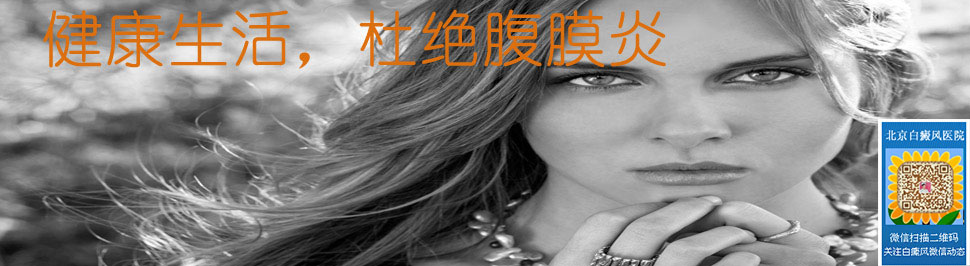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E-Mail:
E-Mail: